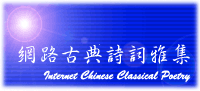有勞望月詞長、錦瑟詞長、李師關注,不勝感激!
步韻絕句係即興之作,不成熟。尤其結句有說教味道,欠妥。
敬盼斧正!
月夜
19 篇文章
• 第 2 頁 (共 2 頁) • 1,2
淼水 寫:最近看了一篇文章.頭腦記憶中只出現.花色.?..女色.?
言物.言事.或是言人...
如果是花色..是指銀柳(貓柳).或是大家所公認的梅花.
如果是指女色......花比人嬌.(當然我不行說.徐娘半老.
風韻......)有一點點李清照的味道..又有一點韋應物的味道...
總歸一句話..只要兩個字.好詩
《毛詩‧序》中說詩有六義,即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。
前三者是體裁,後三者是作法。
所以淼水詞長的高見屬詩的作法問題。
「賦」-做「布」解。朱熹解為「直陳其事」。即言物.言事.或是言人...直截了當敘述之。
「比」-做「譬」解。朱熹解為「以彼狀此」。即言物.言事.或言人用比喻表之。亦就是淼水詞長的高見「...如果是指花色..是指銀柳(貓柳)....如果是指女色....花比人嬌....」。
「興」-做「起」解。宋人范處義解為「因感而興者」。即由於外物觸發作者內在的情志而抒發之。
至於三種作法,孰好孰不好,後學識淺難加評論。朱光潛【詩論】〈詩的境界〉第〈三〉節關於詩的境界幾種分別中,就王國維在【人間詞話】裡提出「隔」與「不隔」之說。朱光潛認為「王說隔如『霧裡看花』,不隔為『語語都在目前』,似有可商酌之處」。於是他又提出「詩原有偏重『顯』與偏重『隱』的兩種。」
末學淺見,這些理論和詩的作法似有直接關係。特不揣陋劣提供同好參酌,若有不當請原諒!
弔影棲遲歲月賒 迢迢悵念赤城霞
長空嘹唳尋歸處 柳綠園田夕照斜
長空嘹唳尋歸處 柳綠園田夕照斜
- 古渡
- 會員
- 文章: 265
- 註冊時間: 2002-10-03 08:55 PM
- 來自: 天台山
19 篇文章
• 第 2 頁 (共 2 頁) • 1,2
誰在線上
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:沒有註冊會員 和 16 位訪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