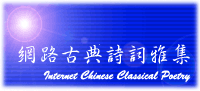第三屆粵港澳臺大學生詩詞大賽徵稿啟事(10/20截稿)
時間 Sat Sep 20 17:11:02 2008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第三屆粵港澳臺大學生詩詞競賽
今年由廣東中山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澳門澳門大學、台灣成功大學四校合辦
收件期間為10/1-20
最高獎金4000元港幣
限四地大學生(不含研究生)參賽
在香港頒獎
徵詩 詩體:五律或七律,韻腳:支、侵擇一)
徵詞 詞牌限<青玉案>,賀鑄、辛棄疾兩體皆可。用運以《詞林正韻》為準。一韻到底,上去聲通叶,入聲單獨叶韻。
詳情請閱http://win2003.chi.cuhk.edu.hk/poetry-comp
第三屆粵港澳臺大學生詩詞大賽徵稿啟事(10/20截稿)
7 篇文章
• 第 1 頁 (共 1 頁)
補充,此比賽原已進行兩屆,原名「穗港澳大學生詩詞大賽」,由廣州(廣東中山大學)、香港(香港中文大學)及澳門(澳門大學)合辯。本屆由廣州擴展至整個廣東省,並加入臺灣,故易名為「穗港澳臺大學生詩詞大賽」。
香港大賽一般不定題,大學組或會限韻,而參賽者須不超碩士資格。比賽最先由這邊中大發起,便依上述慣例。
香港大賽一般不定題,大學組或會限韻,而參賽者須不超碩士資格。比賽最先由這邊中大發起,便依上述慣例。
- 杰
- 會員
- 文章: 3735
- 註冊時間: 2005-06-28 11:16 PM
- 來自: 香港
將原網頁內容整理如下
第三屆粵港澳臺大學生詩詞大賽
詳見詩詞大賽網頁:http://win2003.chi.cuhk.edu.hk/poetry-comp/apply.aspx
◎主辦: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、澳門大學中文系、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、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
◎承辦: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◎參賽資格:香港、澳門、廣東、臺灣四地各公立、私立大專院校、高校二00八年九月持有學籍之大學生(不包括研究生)均可參賽。參賽作品必須為未經發表之原作,頒獎前亦不能在網上發布,倘發現有抄襲及違規成分,則取消獲獎資格。參賽者可單獨參加詩賽或詞賽,亦可同時參加詩賽和詞賽。參賽作品以一首為宜,最多可交兩首,每人獲獎以一首為限。參賽者可以同時在詩賽和詞賽中獲獎。
◎評審方式:參賽作品糊名評選。入選作者須於十一月間在原居地與大賽評委見面,確認其作品之真實性,始得獲獎。未入選者身分予以保密。
◎獎勵方式:詩賽、詞賽各設獎額九名
冠軍一名,獎金港幣4000元。
亞軍一名,獎金港幣3000元。
季軍一名,獎金港幣2000元。
優異獎六名,獎金各港幣1000元。
投稿方式:2008年10月1-20日接受電子投稿,請據http://win2003.chi.cuhk.edu.hk/poetry-comp/apply.aspx網站第三屆粵港澳臺大學生詩詞大賽參賽表格輸入作品及寄出。
稿件必須依格式填寫地區、姓名、身份證號碼、學生證號碼、大專院校、學院學系、班級、電話、電郵、地址各項。
◎詩賽規則 體裁:五律或七律。
題目:作者自定。以簡單明白為主,不宜太長。盡量不用注釋。
用韻:以平水韻或《佩文詩韻》為準,限用上平四支韻或下平十二侵韻。
◎詞賽規則 詞牌:〈青玉案〉。賀鑄、辛棄疾兩體皆可。
題目:作者自定,可以不寫。盡量不用小序,更不宜用長序及注釋。
用韻:以《詞林正韻》為準,不限韻部。一韻到底。上去聲通叶,入聲單獨叶韻。
譜式參考:
凌波不過橫塘路。但目送、芳塵去。錦瑟華年誰與度。月橋花院,瑣窗朱戶。只有春知處。
飛雲冉冉蘅皋暮。彩筆新題斷腸句。若問閒情都幾許。一川煙草,滿城風絮。梅子黃時雨。
(賀鑄〈青玉案〉)
東風夜放花千樹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。鳳簫聲動,玉壺光轉,一夜魚龍舞。
蛾兒雪柳黃金縷。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。驀然回首,那人卻在,燈火闌珊處。
(辛棄疾〈青玉案〉元夕)
第三屆粵港澳臺大學生詩詞大賽
詳見詩詞大賽網頁:http://win2003.chi.cuhk.edu.hk/poetry-comp/apply.aspx
◎主辦: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、澳門大學中文系、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、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
◎承辦: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◎參賽資格:香港、澳門、廣東、臺灣四地各公立、私立大專院校、高校二00八年九月持有學籍之大學生(不包括研究生)均可參賽。參賽作品必須為未經發表之原作,頒獎前亦不能在網上發布,倘發現有抄襲及違規成分,則取消獲獎資格。參賽者可單獨參加詩賽或詞賽,亦可同時參加詩賽和詞賽。參賽作品以一首為宜,最多可交兩首,每人獲獎以一首為限。參賽者可以同時在詩賽和詞賽中獲獎。
◎評審方式:參賽作品糊名評選。入選作者須於十一月間在原居地與大賽評委見面,確認其作品之真實性,始得獲獎。未入選者身分予以保密。
◎獎勵方式:詩賽、詞賽各設獎額九名
冠軍一名,獎金港幣4000元。
亞軍一名,獎金港幣3000元。
季軍一名,獎金港幣2000元。
優異獎六名,獎金各港幣1000元。
投稿方式:2008年10月1-20日接受電子投稿,請據http://win2003.chi.cuhk.edu.hk/poetry-comp/apply.aspx網站第三屆粵港澳臺大學生詩詞大賽參賽表格輸入作品及寄出。
稿件必須依格式填寫地區、姓名、身份證號碼、學生證號碼、大專院校、學院學系、班級、電話、電郵、地址各項。
◎詩賽規則 體裁:五律或七律。
題目:作者自定。以簡單明白為主,不宜太長。盡量不用注釋。
用韻:以平水韻或《佩文詩韻》為準,限用上平四支韻或下平十二侵韻。
◎詞賽規則 詞牌:〈青玉案〉。賀鑄、辛棄疾兩體皆可。
題目:作者自定,可以不寫。盡量不用小序,更不宜用長序及注釋。
用韻:以《詞林正韻》為準,不限韻部。一韻到底。上去聲通叶,入聲單獨叶韻。
譜式參考:
凌波不過橫塘路。但目送、芳塵去。錦瑟華年誰與度。月橋花院,瑣窗朱戶。只有春知處。
飛雲冉冉蘅皋暮。彩筆新題斷腸句。若問閒情都幾許。一川煙草,滿城風絮。梅子黃時雨。
(賀鑄〈青玉案〉)
東風夜放花千樹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。鳳簫聲動,玉壺光轉,一夜魚龍舞。
蛾兒雪柳黃金縷。笑語盈盈暗香去。眾裏尋他千百度。驀然回首,那人卻在,燈火闌珊處。
(辛棄疾〈青玉案〉元夕)
- 維仁
- 版面管理員
- 文章: 4544
- 註冊時間: 2002-02-25 09:24 AM
- 來自: 台灣
偶然中看到了徐晉如先生的文章,深有感慨。一方面對於台灣學界古典詩詞的中衰感到難過,一方面也對彼岸學者於台灣詩壇的錯誤認知感到無奈。(如此中提到大專聯吟至今已舉辦27屆云云)附文於後,更希望雅集的大學生們多多參加投稿。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3e47063f0100ah44.htm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們真的比不過台灣?
由香港中文大学、澳门大学、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大赛办了两届,从今年开始,改为粵港澳台大学生诗词大赛。
改穗为粵,把内地参赛高校的范围扩大到了广东全境,这对很多高校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我曾四次到潮州讲学,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,是詹安泰和饶宗颐先生曾经执教过的学校,人文积淀殊深。我在2003年曾夤缘一往,并作了《杜甫与王维——中国传统诗学的两个体系》的讲座。这个学校在系主任赵松元兄的带领下,十分重视传统文化。他要求所有毕业的学生必须掌握诗词写作的技能。当然,技不等于道,能否由技而进诸道,端的看各人修为了。该校毕业的陈伟贤弟,即是一位优秀的青年诗人,今年端午,他受邀参加了中华诗词(BVI)研究院主办的“2008北京中华诗词(青年)峰会”。
还记得2006年举办首届“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大赛”,在赛事结束商议颁奖事宜时,中大中文系的一位副主任忽然进来,问了一句:这次比赛没有带台湾吧?我们答:没有,就是穗港澳。他的回答让我终身难忘:聪明!我们比不过台湾的!当时听了这话,我们都很难受,觉得他的话可能是实情。台湾在国学传承方面,曾经的确比我们厉害。然而我心里还是不服气,第一,陈水扁上台后大搞去中国化,台湾青少年的国学素养已大不如前。第二,台湾人没有经历我们的苦难,苦难出诗人,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究竟结果如何,我们且待赛事结束分解。
本次赛制,依然延续了香港的经验。而我则更倾向于“台湾大专青年联吟赛”的方法。其方法大致是先从投稿中遴出入围的,再提供资助,让大家到一个地点集中,现场出题,考律诗、绝句各一,同时,还有各校吟诵队的诗词吟诵比赛。如果是我主办,我会要求加上考诗论的环节,一率要求文言答题。不但要见出一个人的诗才,还要见出一个人的识见。
这个联吟赛,迄今已办了二十七年,是由一位陈逢源先生创立了文教基金,专门资助。我师龚云起先生说:“近二十年间,台湾作旧诗的年轻人,大概没有人不晓得陈逢源先生,也没有人不读他的《溪山煙雨楼诗存》。原因无他,陈先生文教基金会在这十几二十年中,不断推广诗教,每年举办全国大专青年诗人联吟大会,间亦办理研习班、印赠诗集及诗韵,所以声华昭著。凡参与诗歌创作或吟唱活动的大专青年,无不知先生及其诗。”这位陈先生是台湾耆宿。在日据时代曾参加台湾文化协会,推动议会设置请愿活动,因而入狱。后任台湾新民报经济主笔。台湾光复后,担任华南银行董事,北区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。又创办台湾农业机械公司、经营台湾炼铁公司等等,是非常成功的实业家。继而又出任省议会第一届议员。可说在政治活动及政治理论方面也都有所表现。但是,龚先生指出:“陈先生最重要的身份,或许仍是诗人;最重要的事功,或许就是建了这座溪山烟雨楼。其诗有云:‘曾抗强权慕自由,老来身世类沙鸥。声喧林鸟笙歌市,诗在溪山烟雨楼。常有娇孙闲绕膝,儘多故纸静埋头。敢誇白鹤新居好,夏木阴森冷似秋。’这座楼,不但为他自己的生涯留下了一个从容俯仰的空间;也替那个时代流棲於海隅的诗人,提供了一处得以相互抚慰、安顿灵魂的场所;更为我辈后学建构了一所得以恣其想像憧憬的诗楼。先生自云:‘诗在溪山烟雨楼’,其实其事功亦在此楼。”
台湾的传统如是。香港的情况尤不容小觑。香港中央图书馆每年举办全港诗词大赛,分社会组与学生组,单年比诗,双年比词,另有香港学界诗词大赛,丰富得很。而且不论是台湾还是香港,他们的高校中文系都把《诗选与诗的写作》、《词选与词的写作》当作必修,另外还有《曲选与曲的写作》以供限选。这种踏踏实实的精神,是内地高校所无法比拟的。前年遇见香港浸会大学一位荣休教授,他说起北大中文系的某位女教授,被香港浸会大学聘去接他的班,这位女教授不会作诗词,根本讲不了写作,很多学生又找他诉苦。广东老诗人李汝伦先生在给拙著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的序中说:“我曾多次在各种会上呼吁大学文学系恢复诗词写作教学,人微则言轻,话音落在死水水面。老教授们已从闭嘴到闭目,灵魂游荡于山阴道上。他们的弟子也大都鬓发飞霜,而且本身也曾是‘不宜提倡’的对象。这些教授中除自学自悟者外,很多连旧时幼学读本也没见过,弄不清哪个汉字姓平,哪个汉字姓仄。堂堂大学,堂堂教授,真是煞透了风景,咄咄怪事。我的呼吁证明我无知,我不会审时度势。”对内地高校教育现象我们哀其不幸,又怒其不争。希望这次粵港澳台的大赛,能对内地高校多一些触动。你们不要再用那些陈旧的文学史来毒害青年了!一定要让青年读原典,要自己学会咀嚼。
忽然想起原复旦大学的教授刘大杰,他旧学根底浅,不会作诗词,四十年代去四川大学任教,结果被学生赶走了。他后来成名,靠的是毛泽东对他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的赏识。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3e47063f0100ah44.htm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們真的比不過台灣?
由香港中文大学、澳门大学、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大赛办了两届,从今年开始,改为粵港澳台大学生诗词大赛。
改穗为粵,把内地参赛高校的范围扩大到了广东全境,这对很多高校的同学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我曾四次到潮州讲学,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,是詹安泰和饶宗颐先生曾经执教过的学校,人文积淀殊深。我在2003年曾夤缘一往,并作了《杜甫与王维——中国传统诗学的两个体系》的讲座。这个学校在系主任赵松元兄的带领下,十分重视传统文化。他要求所有毕业的学生必须掌握诗词写作的技能。当然,技不等于道,能否由技而进诸道,端的看各人修为了。该校毕业的陈伟贤弟,即是一位优秀的青年诗人,今年端午,他受邀参加了中华诗词(BVI)研究院主办的“2008北京中华诗词(青年)峰会”。
还记得2006年举办首届“穗港澳大学生诗词大赛”,在赛事结束商议颁奖事宜时,中大中文系的一位副主任忽然进来,问了一句:这次比赛没有带台湾吧?我们答:没有,就是穗港澳。他的回答让我终身难忘:聪明!我们比不过台湾的!当时听了这话,我们都很难受,觉得他的话可能是实情。台湾在国学传承方面,曾经的确比我们厉害。然而我心里还是不服气,第一,陈水扁上台后大搞去中国化,台湾青少年的国学素养已大不如前。第二,台湾人没有经历我们的苦难,苦难出诗人,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究竟结果如何,我们且待赛事结束分解。
本次赛制,依然延续了香港的经验。而我则更倾向于“台湾大专青年联吟赛”的方法。其方法大致是先从投稿中遴出入围的,再提供资助,让大家到一个地点集中,现场出题,考律诗、绝句各一,同时,还有各校吟诵队的诗词吟诵比赛。如果是我主办,我会要求加上考诗论的环节,一率要求文言答题。不但要见出一个人的诗才,还要见出一个人的识见。
这个联吟赛,迄今已办了二十七年,是由一位陈逢源先生创立了文教基金,专门资助。我师龚云起先生说:“近二十年间,台湾作旧诗的年轻人,大概没有人不晓得陈逢源先生,也没有人不读他的《溪山煙雨楼诗存》。原因无他,陈先生文教基金会在这十几二十年中,不断推广诗教,每年举办全国大专青年诗人联吟大会,间亦办理研习班、印赠诗集及诗韵,所以声华昭著。凡参与诗歌创作或吟唱活动的大专青年,无不知先生及其诗。”这位陈先生是台湾耆宿。在日据时代曾参加台湾文化协会,推动议会设置请愿活动,因而入狱。后任台湾新民报经济主笔。台湾光复后,担任华南银行董事,北区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。又创办台湾农业机械公司、经营台湾炼铁公司等等,是非常成功的实业家。继而又出任省议会第一届议员。可说在政治活动及政治理论方面也都有所表现。但是,龚先生指出:“陈先生最重要的身份,或许仍是诗人;最重要的事功,或许就是建了这座溪山烟雨楼。其诗有云:‘曾抗强权慕自由,老来身世类沙鸥。声喧林鸟笙歌市,诗在溪山烟雨楼。常有娇孙闲绕膝,儘多故纸静埋头。敢誇白鹤新居好,夏木阴森冷似秋。’这座楼,不但为他自己的生涯留下了一个从容俯仰的空间;也替那个时代流棲於海隅的诗人,提供了一处得以相互抚慰、安顿灵魂的场所;更为我辈后学建构了一所得以恣其想像憧憬的诗楼。先生自云:‘诗在溪山烟雨楼’,其实其事功亦在此楼。”
台湾的传统如是。香港的情况尤不容小觑。香港中央图书馆每年举办全港诗词大赛,分社会组与学生组,单年比诗,双年比词,另有香港学界诗词大赛,丰富得很。而且不论是台湾还是香港,他们的高校中文系都把《诗选与诗的写作》、《词选与词的写作》当作必修,另外还有《曲选与曲的写作》以供限选。这种踏踏实实的精神,是内地高校所无法比拟的。前年遇见香港浸会大学一位荣休教授,他说起北大中文系的某位女教授,被香港浸会大学聘去接他的班,这位女教授不会作诗词,根本讲不了写作,很多学生又找他诉苦。广东老诗人李汝伦先生在给拙著《大学诗词写作教程》的序中说:“我曾多次在各种会上呼吁大学文学系恢复诗词写作教学,人微则言轻,话音落在死水水面。老教授们已从闭嘴到闭目,灵魂游荡于山阴道上。他们的弟子也大都鬓发飞霜,而且本身也曾是‘不宜提倡’的对象。这些教授中除自学自悟者外,很多连旧时幼学读本也没见过,弄不清哪个汉字姓平,哪个汉字姓仄。堂堂大学,堂堂教授,真是煞透了风景,咄咄怪事。我的呼吁证明我无知,我不会审时度势。”对内地高校教育现象我们哀其不幸,又怒其不争。希望这次粵港澳台的大赛,能对内地高校多一些触动。你们不要再用那些陈旧的文学史来毒害青年了!一定要让青年读原典,要自己学会咀嚼。
忽然想起原复旦大学的教授刘大杰,他旧学根底浅,不会作诗词,四十年代去四川大学任教,结果被学生赶走了。他后来成名,靠的是毛泽东对他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的赏识。
今古恨 幾千般 只應離合是悲歡
- 何維剛
- 會員
- 文章: 632
- 註冊時間: 2002-05-16 01:45 AM
- 來自: 水月
何維剛 寫:偶然中看到了徐晉如先生的文章,深有感慨。一方面對於台灣學界古典詩詞的中衰感到難過,一方面也對彼岸學者於台灣詩壇的錯誤認知感到無奈。(如此中提到大專聯吟至今已舉辦27屆云云)附文於後,更希望雅集的大學生們多多參加投稿。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3e47063f0100ah44.htm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......
或者就像中國人傳統思維那樣,「人家的月亮總是圓的」。徐先生上帖末學回覆過。他另有《大學中文系都應該把詩詞寫作列為必修》一文,此中引用末學與另一位雅集詞長之掄元作,兼談香港詩壇(但實情沒那麼樂觀)。臺灣已經比香港好,香港炒股第一、炒樓第二......
也望雅集諸位踴躍參加!
- 杰
- 會員
- 文章: 3735
- 註冊時間: 2005-06-28 11:16 PM
- 來自: 香港
7 篇文章
• 第 1 頁 (共 1 頁)
誰在線上
正在瀏覽這個版面的使用者:沒有註冊會員 和 13 位訪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