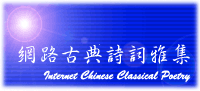張栩 寫:「灑豆腴田不使荒」、「焚草聞煙渾欲醉」,欣賞!小時候也聞過焚草煙,是有股甜腥氣,此境應該從沒人說過?
再來勉和一首:
芝田人境隙
壟上朮蒼蒼
地美農庸勸
詩新稅可償
科頭朝兀傲
捫腹晚彷徉
秋播定須我 (須,待也)
耦耕歌楚狂
南山子詞長寫了擬寒山詩。想起世俗畫卷,都是寒山與拾得一起,則末學與芝言詞長,當個長沮桀溺如何?但末學顯然是攀附了
又一首詩飛來,(還是有點深奧,恕我書讀得不多)一時間彷彿已經是勤農,果不亦起勁乎?
再加上攀附說,害我兩天不知如何回答。
如真有值得攀附之處,我只有覺得榮幸,還會捨不得嗎?
只是,癩痢頭照鏡子,坑坑疤疤,東一撮西一撮的,別人家都搖頭,只有我嗜痂成性還撰文作詩頌讚之,以為有多好。
不稼不蔬是讓她有無限可能的發展,宛如胸中藍圖,一旦成形了就是其他所有幻想的破滅了,何必呢?
說笑話,長沮桀溺應該也不想、也當不成現代農夫;現代化失韻味,原始化種不到吃的。實耕既不可行,還是多動腿後多動筆更合軟腳蝦都市人的吧?
我夢如爾夢,田與不田皆非田,
硯田炷香巡即畢,耦耕何如雙耦耕?